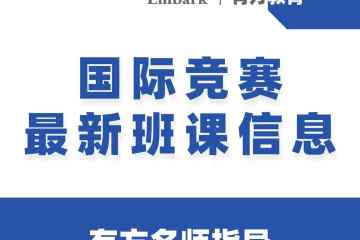哈佛博士谈:90%准留学生都不知道怎么做学术研究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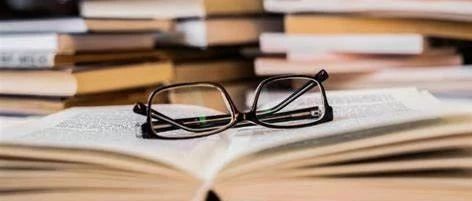
魏阳老师: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、现在科罗拉多大学任教。
知识只是“暂时的”
我认为,大学的目标有两个,一个是传授已有的知识;另一个,是创造新的知识。前一个目标,是所有大学共享的。而后一个目标,是好大学与普通大学的区别。一个好的大学,无论是人文学科、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,都遵循同一个研究原则:应该告诉学生,现有的结论,永远不是绝对的。任何人,无论多么有权威,都有可能犯错误。即使是学科里的前辈和巨人也可能犯错误。大学教育的目标,是学习一种研究的方法,去不断从新的角度,检验、修正、改写以前的认知,拓展知识的新边疆。换句话说,我们现在对自然、社会、对人自身的认识,无论看起来多么“权威“,多么“传统”,都只是“暂时”的知识,不是永恒的。在研究方法不断进步的同时,所有现在公认的知识,都有可能被推翻,被修正,被改写。
许多你以为是“常识”的知识其实都是错误的比如: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曾经说,北京猿人是中国人的直系祖先。后来随着史前考古学和基因工程的进步,我们才知道,中国人绝大部分的基因,并非来自已经在东亚大陆生活了数十万年的直立人,而是来自走出非洲的,大约在六万年前来到东亚的智人。中国人的基因来源也很多样。智人走出非洲之后,与从中东到东亚的早期直立人都发生过交配的行为,所以现在的东亚人也会有其他早期人类的基因。比如,东亚人和高加索人种一样,都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。此外,现代东亚人还携带着中亚的丹尼索瓦人的基因。而留在非洲的人类,则没有这些基因。
研究手段的变化,不断改写我们的知识,拓展认知的新边疆。
同样,以前人们认为,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是“闭关锁国”的。我们曾经相信,是清政府的自我孤立,导致了中国的“落后”。但是近来的研究发现,与之前的朝代相比,清代是一个外向拓展型的帝国。与之前的中国王朝相比,清代更注意向中亚内陆扩张,将西藏、新疆、蒙古纳入版图,建立一个“世界性”的帝国。在东南沿海,也一直有繁荣的贸易。整个清朝,虽然政府一直试图控制对外贸易,但是中外的货物和思想,始终在通过合法和走私的方式,源源不断的越过边界。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:如果清朝真的“闭关锁国”,那么鸦片战争之前,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抽进口的鸦片,白银怎么会外流呢?“锁国”这个概念,可能来自于1630年代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“锁国”政策。说清朝“闭关锁国”,是一个错误的认知。
怎么做研究?
这里有两个通用方法。我们对于自然、社会、和人自身的认知,总是在不断的改变。大学的目标,不是让人们相信某种已有的知识和观点,而是让人怀疑这些知识和观点。用一套符合逻辑,有证据支持的方法,来获得新的知识。那么,学生该如何找到自己的研究兴趣,提高研究能力呢?我再举几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例子。在论文的写作开始之前,很多学生会很困惑,感觉找不到好的研究题目。这时,我一般会向他们介绍两种方法:
● 第一种方法,是从问题出发。
● 第二种方法,从材料和数据出发。
今天,我们先详细讲第一种。从问题出发,是指先提出一个研究问题,然后去看前人有没有已经做过研究?这些研究是否让人满意?如果不满意,那么通过什么其他方法和手段,能够获得新的证据和数据,验证以前的结论?这种方法,要求学生质疑现有的观点。“宫保鸡丁”原来不是“正宗”中国菜?比如,很多人认为,中国的烹饪源源流长,似乎和其他的中国传统一样,是从古代传下来的。不少读物,也纷纷这么暗示。但是,如果你不人云亦云,就会问:现在流行的菜肴,比如宫保鸡丁,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?这让你去认真寻找答案。老师的作用,不是告诉学生答案是什么,而是告诉他们,寻找答案的方向大概是怎样的,让他们自己去寻找答案。比如,想知道宫保鸡丁是何时出现的,我会让学生去查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论文数据库搜索,这是一个免费的网上论文数据库,很方便。在欧美,类似的英文数据库也有很多,包括JSTOR和EBSCO。检索这些研究论文数据库,都是研究必须的。
在搜索完毕之后,你会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堆论文,外加数本专著——这些被统称为研究文献。这时你要通读这些文献。对你的研究重要的文献,要认真读。关系不密切的,可以迅速浏览,看看摘要即可。在高中和大学阶段的研究问题,很多可以通过阅读前人的研究得以解答。如果以前没有研究的,可以进行社会调查,实验,采访,搜集其他原始数据材料,并加以分析,得到初步的答案。比如宫保鸡丁的起源,可能有人已经做过研究。即使以前没有研究,但我们从逻辑上可以推知,花生和辣椒,这两个宫保鸡丁的必要原料,都是从美洲传入的。而欧亚大陆的人,在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,是不清楚美洲的。美洲的农作物,比如辣椒、华生、土豆、蕃薯、都必须要在哥伦布之后,才有可能传到中国。所以,宫保鸡丁,在中国出现的时间,不可能早于明代晚期。另外,关于中国烹饪史的其他研究也会表明,在油锅里用大火爆炒的烹饪方法,是在晚明和清代才开始流行的。这也进一步佐证了宫保鸡丁这样家常中国菜,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,其实是很晚近的。这个例子也说明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。我们以为的、“正宗”、“经典”的中国菜,不仅出现时间很晚,而且甚至不完全是“中国”的。显然,如果没有美洲传入的食材,就不会有这些中国菜。所谓正宗的中国菜,不过是全球化的产物,是世界文明交流的产物。
用“宫保鸡丁”刷新三观
这时,你甚至可以得出一个看似大胆的结论。所有“正宗”、“经典”的菜肴,追其源流,可能都是一些“杂种”(hybrid),都是文明之间不断交流的产物。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“正宗“的,一切都是在历史中变化着产生的。遵循同样的逻辑,你会质疑所有我们认为一成不变的“传统”。我们所认为的中医、农历、儒学、宗教、葬礼、姓氏这些“传统”习俗,可能都并非如我们想象得那样古老和一成不变。更进一步的,你可能由此反思社会流行的思维方式。我们认为是传统的东西,到底有多少是在某个很晚近的时间点才出现。也许,所有的“传统“,不过都是某个特殊历史时期的“创新”,然后不断变化直到今天?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:
● 如果所有的“传统”不过是历史某个时期的“创新”,为什么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我们的传统是源远流长、牢不可破的?
● 到底是谁,在编造一成不变的“古老”传统这样的神话?出于什么目的?这样,你的研究就会走入更深一层次的探讨。
回到上面说的中国明清的“锁国”政策。从明代到清代,几乎没有人说中国曾经有“锁国”政策。只有到了清末,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去日本,了解到了日本德川时期的“锁国令”,再拿来比附中国以前的情况,于是得出了中国也曾经“闭关锁国”的印象。在191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,通过当时的“网红”作家梁启超和陈独秀等人的大力弘扬,渐渐的,大家都以为中国历史上也和日本一样,有过一个“锁国”的时代。直到今天,还有很多人写论文说中国有一个“锁国体制”。“锁国”的说法,虽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,但却反映了近代中国人,对于自己国家开放程度不够的一种焦虑。
再比如,我们今天说中国人是炎黄子孙,是龙的传人。可是,细读历史就会发现,中国古人并不会这么说。在传统时代,只有皇家,才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,才能用龙的图案。炎黄子孙、龙的传人的说法,也是从晚清和民国年间才开始的。那时,中国正从一个有诸多民族的帝国,向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转型。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,想仿照欧洲,把中国建造成一个有单一民族认同的国家。所以,人们创作出了“中华民族”这个概念,和炎黄子孙这个概念一起,用来包括所有中国境内的居民。
这个说法告诉我们,无论你说什么语言,信仰什么宗教,头发眼睛皮肤是什么颜色,遵从什么文化习俗,你们都来自同一个传说中的同一个祖先。新传统的诞生,不是随机和偶然的,背后有着社会结构变化的深层原因,表达了人们在某一个历史时期重要的动机和目的。炎黄子孙的神话,正说明在近代中国塑造单一民族认同的挑战与困难。
“从问题出发”的方法会给学生带来哪些帮助?
我常常问学生的一个问题是,互联网科技,是增加还是减少了人们选择信息的自由?你在直觉上可能认为,互联网当然是增加了人们的自由。因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,更便捷的生活方式,更多的信息,更多的选择权利。但是也有人认为,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,总是有限度的。能接触到的信息,也是有限度的。而信息获取的便捷,让我们倾向于只获得自己喜欢的内容和赞同的观点。而很多平台对大数据的应用,也让平台只推送我们感兴趣并赞同的内容。结果是,我们离自己不熟悉的信息,和自己不赞同的观点,越来越遥远。现在建立微信群很方便,但结果是,我们只留在自己认同的群里(因为退群太方便),回避与自己观点立场不同的人。久而久之,我们仿佛活在一个蚕茧里的蚕,只活在一个自己的小世界里,只和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人进行交流,只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互联网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信息交流。信息的丰富,却让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小。这被叫做“蚕茧效应”或“信息茧房”。
更危险的是,在这种情形下,如果一旦平台有选择的推送某种信息,过滤掉其他信息,人们会变得很容易被操纵。比如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,美国的脸书,就被指控为被人利用操纵舆论,在政治观点上误导用户。这么说来,互联网看起来让人们自由选择信息,实际上减少了人们广泛交流、选择信息的自由。
更危险的是,仿佛奥威尔的小说《1984》中寓言的场景:互联网科技让人在被操纵的同时,误以为自己享有自由。《1984》书籍封面从问题出发选择研究题目,是开放性的。你会发现,大部分的问题,都可以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回答。你既可以说互联网增加了人们的自由,也可以论证互联网限制了人们的自由。
社会与人文的研究,既要遵循严谨的方法,同时也是一门艺术,给你相当大的空间自由发挥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经过这样训练的学生,能够理解,没有任何一种角度、学科和模型,能够完全理解社会和人类本身。只有从不同角度,用不同的方法,不断探索认知的新边疆,挑战已有的结论,我们才能认识人类社会的极端复杂性。
本文授权转载自“爸爸真棒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