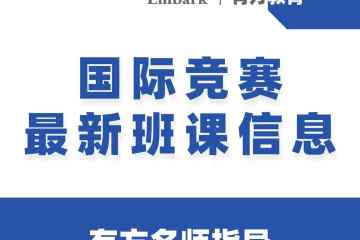古人的游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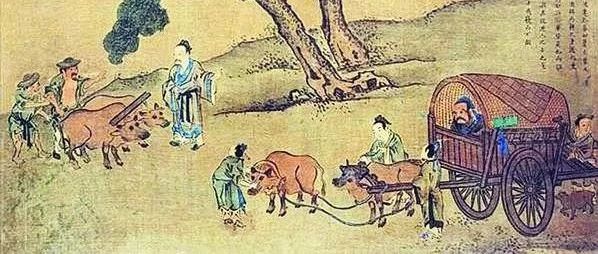
游学并不是舶来品,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,古人就有了游学这项活动。史学家吕思勉曾经考证过游学的历史记录:“游学”二字见《史记·春申君列传》,曰:“游学博闻,盖谓其因游学所以能博闻也。”
在中国历史上,首先提出游学概念的是先秦的诸子百家,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进行治学,庄周更是自由自在地逍遥游,游学一方面作为他们通晓经术、拜访名师乃至学而优则仕的一种途径,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。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“游学”二字掀起了一阵复古风、倏地就时尚了起来。出门远行,和山水亲热,吞吐外埠菁华,或者招呼上三两好友,把自嗨升级成群嗨,如此游学其实更像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为了正本清源,我们有必要将游学的历史渊源拉扯拉扯,搞清楚什么才是“游学”。
古今游学有啥区别
现代教育意义上的游学,是指大中院校、社会机构和博物馆等通力合作,面向国内外有需要人群,开设游学课程,积极鼓励并正确引导他们融入到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环境中,通过亲自体验来学习当地的文化与习俗。
最早将游学引申为“出国学习”的是清代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张之洞。张之洞在他的《劝学篇》中说到: 游学之益,幼童不如通人,庶僚不如亲贵,尝见古之游历者矣。
晋文公在外十九年,遍历诸侯,归国而霸。
赵武灵王微服游秦,归国而强。
春秋战国最尚游学,贤如曾子、左丘明,才如吴起、乐羊子,皆以游学闻。
其余策士杂家,不能悉举。
古代游学类型
那么古代的游学又是个什么玩法呢?翻查资料,我们可以看到有关游学的四类直观描写:
1.游侠和儒生;
2.从事游说的人,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里写道“异时诸侯并争,厚招游学”,这里的游学说的就是苏秦张仪这样的专擅合纵连横的国嘴大咖;
3.离开本乡到外地求学的人;
4.宴游与学习的人,泡泡饭局吃吃喝喝也算游学?可是司马光点头说Yes,《资治通鉴·汉元帝建昭四年》里说的明白,“游学,游谓宴游,学谓讲学”。司马光都说是,别人就认了吧。
游学还是中国古代比较常见的教学方式,分为教师周游讲学和学生出外游学两种。孔、孟、荀等大教育家都曾在周游列国中教育学生,战国时期的权臣养士,士人游学以结党盛行一时。
西汉经学家郑玄也是“游学周秦之都,往来幽、并、兖、豫之地”。对古时教育家来说,周游讲学是他们传播其教育思想的方式之一。对于文人学者来说,游学四方可能就成了一张镀金的名片,一旦拥有,风光得很。
古人有个绵延至今的优良传统就是云游四方,拜访各地知名学者,仆倒行礼,愿充门下,或是当面请教不解难题,即便未结师生之缘,也是你来我往,彬彬有礼。古代学子云游四方非常辛苦,不像现在可以借助网络,做到秀才不出门,便知天下闻。但知识这东西并不是你知道就行,现代人一般不是去探求知识的本源,只是了解知识,未做到融汇贯通,不像古代学子那样一叶知秋,说明现代人做学问只是堆砌知识,而没有得到最深的智慧。真正的知识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协调,是人与外界的和谐,是真正了解事情本源的东西。
耳提面命也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,给了学习者一种对于知识的态度。这一点是需要今天的人学习的。
越是高级的事物,越是会跨越地域、种族,形成全世界共通的标准。比如游学,意大利旅行家马可·波罗在中国的游历,也透露出古代东西方游学交流中蕴涵的丰富信息。
古人游学事迹
中国自古以来就格外看重游学对人格养成和知识形成的引导作用,孔子率领众弟子周游列国,增进弟子学识,培养弟子品质,开阔眼界,而且在游学过程中,事事皆有启发,可谓处处皆为吾师,即便是大儒孔圣,也会遇到“两小儿辩日”这样的醍醐灌顶。这样机缘偶遇的造化,一定是游学途中才能遇上的幸运。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,为后世留下传承至今家喻户晓的教育古训,它所带来的益处是不言而喻的。
孔子周游列国,被视为游学精神的鼻祖,海外游学的宣传册也时常抬出这位老祖宗,以示源远流长。但孔子和他的学生们所经历的艰辛困苦与人生体验,显然是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型游学无法望其项背的。孔子在游历中体悟人生,并将种种体悟传递给追随他的弟子,兴之所至,便在杏树下开坛讲学,杏花纷飞处,渐渐有了《论语》,有了“杏坛”。这幕天席地的课堂,如同佛经中拈花微笑的刹那,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处最富于诗意的一页。
宋代是个重文轻武的朝代,游学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讲学和求学方式。宋代的一些大教育家,民间收徒的学者,条件较好的书院、义塾等公开接纳游学之士,形成了学者周游讲学和游士出外求学的教育良性大互动。
私学在宋代较为活跃。宋代私学教育具有更大的适应性,可以因时、因地、因人而设,满足各种不同的要求。这一百花盛开的局面,特别适合于游学这种教学形式,这也是私学教育在当朝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之一。
虽然私学规模较官学为小,但因私学收费低廉,所以受贫寒士子青睐,更受各方游学之士欢迎。宋代许多布衣寒门出身的名臣,如大名鼎鼎的范仲淹,在其青少年时期就曾有过游学于私塾读书的经历。宋代私学兴盛,私学的开办条件简单,因陋就简,主要靠主讲教师的声望作号召,他们或因不愿入仕,或因在家侍奉老人,或因退休还乡,或因四方游历讲学,或因官职升迁,慕名登门造访的游学之士络绎不绝。
宋代文人学子向往游学,其实还有可做不可言、可意会不可挑明的潜规则在里面。通过学习知识,为以后做官显达创造条件。宋代各地教育发展是不平衡的,京城和江南地区的教育程度远高于其它地区,所以各个学生都愿意游学于教育发达地区,学到在乡间僻壤学不到的知识,结识一些原本见不到的名师硕儒,为以后的援引提携创造有利条件。因此,京都及江南一带,成为众多游学之士汇聚的中心,官学和民间私学的游学都普遍流行。
宋儒读书,多以功名利禄为先念,很多人为了得到出仕的机会,游历天下,结交权贵,形成了大规模的游学之风,这种风气对游学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求知与求仕的动机一样,是儒士希望通过游学改变自身的处境,反映了儒士们对生活、理想的追求。
汉魏时期的北海朱虚(临朐旧称)人邴原,自小聪明好学,随着年龄的增长,他深感单从书本上学知识不够用,于是他想到了到外地游学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,顺便扩大一下朋友圈。邴原本是个很喜欢喝酒的人,有终日不醉的海量。
然自从他开始游学之后,因为怕嗜酒会耽误学业,竟整整八九年间滴酒不沾。其间,每当游学结交的好师友们设宴款待他时,他总是托辞自己不会喝酒。就这样,通过多年四处求学,他的学识大有长进。后来由于他学识渊博,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,游学之士,教授之声不绝。
”返回家乡后,他又设置学堂,“讲述礼乐,吟咏诗书”,创立了以品德高洁著称的邴原学派,并被世人誉为“国之重宝”。后被曹操发现,征召他为丞相征事,又批准他“代凉茂为五官将长史”。由此可见,一边学好知识,一边坚守情操,不改初衷,才是游学的至高境界。 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幼年好学,博览图经地志。22岁那年,他头戴母亲做的远游冠,肩挑简单行李离开了家乡。三十多年里,游历了十六个省,东到普陀山,西到腾冲,南到南宁,北至蓟县盘山,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徐霞客旅途中备尝艰险。其观察所得,按日记载。死后季会明等整理成颇具地理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《徐霞客游记》。
李白25岁时出川辞亲远游,经成都、峨眉,乘舟东下,紧接着又东出三峡,见到了唐玄宗前往泰山举行封禅仪式的浩荡队伍,大开了眼界。后来又感受到了十里扬州的富庶和长安的富贵与威严。离开京师后,一路东行,来到东都洛阳与杜甫第一次相遇……此后数年,他南下宣城,北游幽州,一边在大唐漫游,一边吟诗作赋。
从古人的一些游历事迹中也可以看出,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。游学确实能够让人增长学识,看更多的风景,在旅途中获得更多的体验与学习。